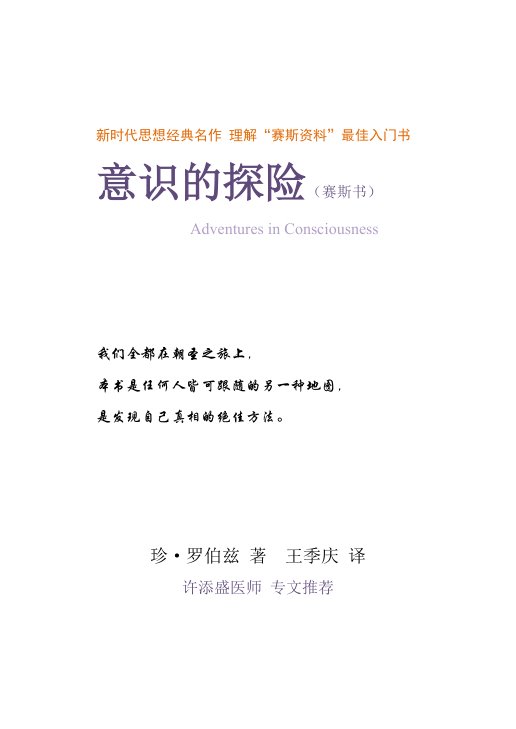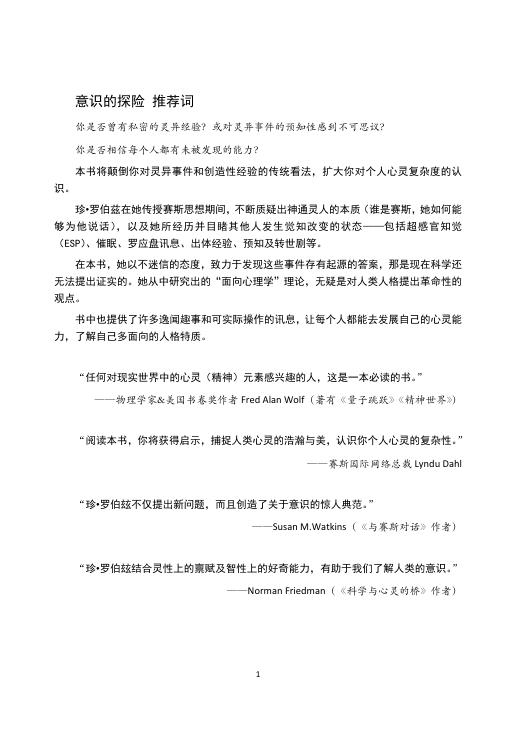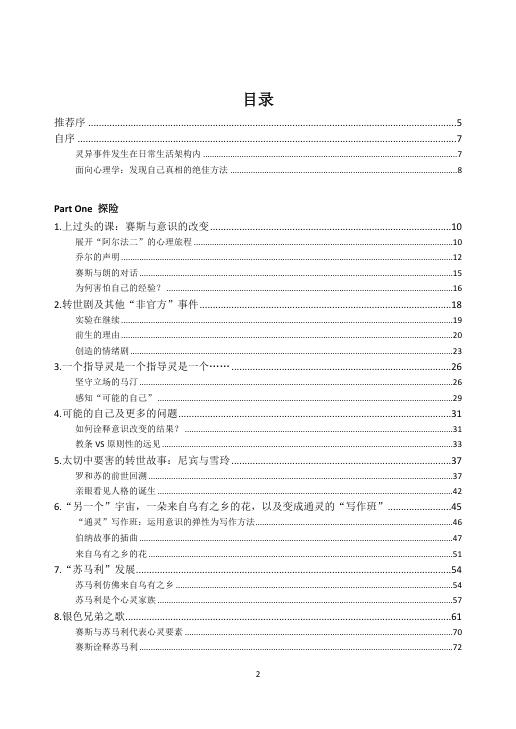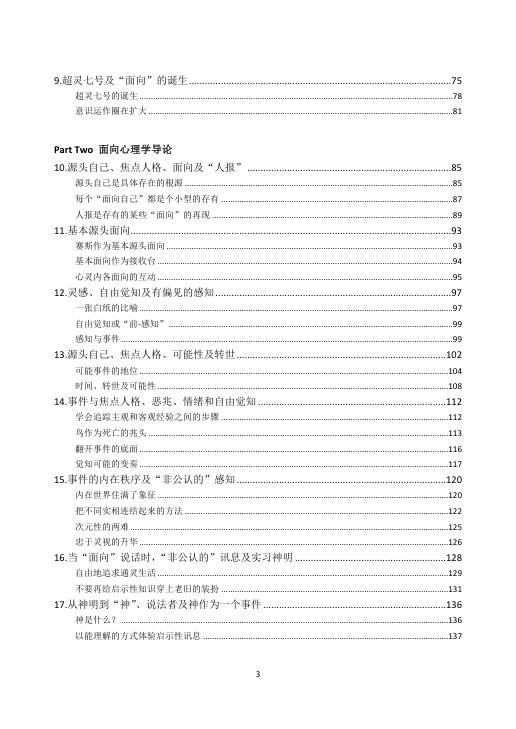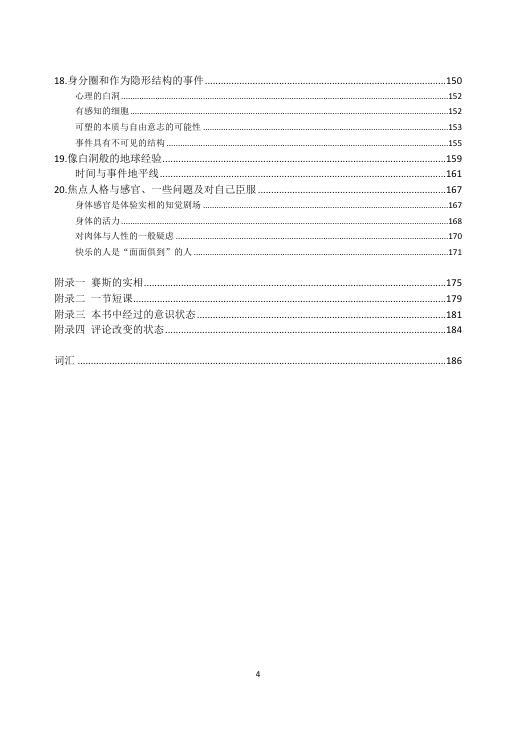生活中,一举一动,事无巨细,都在我们意识的主导下在展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小至个人大至国家乃至国际社会全人类这个大集体,各种意识交织,主导我们人类文明向前发展。可是又有几人会清晰地认识到意识对自身乃至社会发展产生的深刻影响呢?
影片中,年仅16岁的年轻物理博士李天,通过对意识的探索研究,认为:世界上的人们只不过使用了大脑区域18%的意识,那么再深入探索下去,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若是运用得当,又能否通过这方面的探索研究再结合各种前沿科技,有效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种种困境呢?从而进一步打破瓶颈,推动我们的文明大幅前进呢?
科技的进步,基础科学的各种探索研究,面对当前的气候问题、地震、火山喷发等地质问题等等,我们在意识领域的探索研究,能否给我们的未来再添希望呢,拭目以待……
导语:进一步了解意识的起源和运作模式不仅有助于找到治疗大脑损伤和恐惧症的新方法,也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我们自己。
20世纪90年代,神经科学家Melvyn Goodale开始研究一种叫做视觉形式失认症(visual form agnosia)的疾病。罹患这种疾病的人不能有意识地分辨眼前物体的形状或方向,但是他们的行为又表现得像他们能看见这些物体一样。“如果你在他们面前拿起一支铅笔,问他们铅笔是水平的还是垂直的,他们是回答不出来的,”加拿大韦仕敦大学大脑与精神研究所创始主任Goodale说,“但奇怪的是,他们可以伸手去抓住铅笔,而且手的方向完全正确。”
来源:Sam Falconer
Goodale最初的研究方向是大脑如何处理视觉相关信息,为此他对有意识和无意识视觉体系进行了观察记录,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研究引起了哲学家的注意,他们把他拉入了关于意识问题的探讨中——当科学遇到哲学,二者都已为之改变。
依靠新型脑活动检测技术,科学家得以进一步完善他们的意识理论——意识是什么、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界限在哪里。随着对意识的了解逐渐深入,一些研究人员开始思考如何对意识进行操纵以治疗大脑损伤、恐惧症和心理精神疾病,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精神分裂症。
但即便研究不断推进,科学和哲学思想不断融合,最基本的问题却仍然没有答案。“我们对于意识是如何产生的这一问题仍一筹莫展。”英国苏塞克斯大学萨克勒意识科学中心副主任、认知和计算神经科学家Anil Seth说。
无反应等于无意识?
意识通常被描述为大脑的主观体验。哲学科学家、巴黎索邦大学在读博士Matthias Michel说,最基础的机器人可以无意识地检测颜色、温度或声音等条件,但意识则会描述与这些感知相关的定性感觉,并包含思考、交流、联想等深层过程。
Michel表示,其实科学家们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开发出了和现在相似的意识研究方法。但意识研究在二十世纪却始终不见起色,因为心理学家并不认可内省法,而仍将注意力集中在可观察的外化行为和引起这些行为的刺激上。即使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认知科学已经建立,意识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科学家们公开质疑它是否是一个站得住脚的科学研究领域。诺贝尔奖获得者、分子生物学家 Francis Crick 在其职业生涯早期曾想过要以意识为研究方向,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实实在在的DNA。
尽管如此,杰出的科学家们(包括Crick)终究还是决定着手解决意识的问题,由此带来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思维转变,当然这也得益于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fMRI)等大脑扫描技术的日益普及。自那时起,科学家们终于开始探索与有意识的信息处理相关的大脑机制。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重大的科研突破,其中包括一名23岁女性的案例:她在2005年7月的一场车祸中遭受严重的大脑损伤,整个人处于无反应状态,或者叫做清醒无意识状态。她可以睁开眼睛,拥有睡眠-觉醒循环,但对于指令无反应,也没有任何自主运动的迹象。车祸发生五个月后她依然处于这样的状态。当时在英国剑桥大学,现如今在韦仕敦大学工作的神经科学家Adrian Owen和他的同事们开展了一项史无前例的研究,他们向患者发出一系列口头指令,在此过程中同时使用fMRI对该患者的大脑活动进行监测【1】。当团队要求该患者想象打网球时,他们观察到她大脑中的辅助运动区(supplementary motor area)出现了活动。团队又让她想象穿过自己家,结果患者大脑中三个与运动和记忆相关的脑区活动明显增加。健康志愿者接到相同的指示时,其大脑中也会有类似表现。
部分患者看起来对外界刺激无反应,但是其大脑活动与健康个体的类似。来源:Adrian M. Owen
Seth说,部分昏迷的人可能存在意识这一发现对于神经科学而言具有变革性意义。这项研究表明,一部分看似对医生、家人无反应的人其实可以理解语言,甚至可能可以进行交流。
在Owen的研究发表后的数年里,大量脑损伤患者研究提供了更多支持性证据——在多达10-20%的无反应患者中可以检测到意识存在的迹象。2010年的一项研究使用fMRI对来自比利时和英国的54名大脑遭受严重损伤的患者进行了监测。当这些患者被要求想象打网球或在他们的房子或城市中行走时(与当初Owen的研究方法类似),共有5名患者表现出大脑活动的迹象【2】。这5人中有2人从未在传统床边评估中表现出任何意识的迹象。
科学家们也开始尝试不再给予口头指令而进行意识监测的方法。在2013年开始的一系列研究中【3】,米兰大学的神经科学家Marcello Massimini及其同事使用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在大脑内制造“回声”并用脑电图进行记录。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学家Martin Monti表示,这种方法就好比敲击大脑,原理跟敲墙估测墙的厚度是一样的。当一个人处于全身麻醉或无梦睡眠状态时,制造出的“回声”会非常简单。但是如果是有意识的大脑,“回声”将会非常复杂并会在大脑皮层(大脑外层)表面广泛传播。该研究结果或有助于开发新的意识检测工具,用于那些无法看到、听到或响应口头指令的人。
定位,定位,还是定位
随着意识检测技术的逐步成熟,科研人员已经开始着手确定哪些大脑区域和神经回路对于意识的产生最为重要。但是在神经方面,关于意识的构成仍存在很多分歧,特别是那些对意识产生最重要的大脑过程和区域。
至少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家就已经知道大脑皮层对意识很重要。新的证据进一步强调了负责感官体验的后皮质“热区”。例如,在2017年的一项睡眠研究中,研究人员在夜间不断唤醒受试对象,同时用脑电图对其进行监测【4】。大约30%的时候,从睡眠中被叫醒的受试对象报告他们在醒来前没有特别的体验。研究表明,睡眠期间没有意识体验的人在醒来前,其大脑的后皮质区域存在很多低频活动。而那些报告自己醒来前在做梦的受试对象,其后皮质区域低频活动明显减少,高频率活动显著增加。因此,研究人员认为也许可以通过对后皮质进行监测,预测受试对象在睡眠期间是否在做梦——甚至可以预测他们梦的具体内容,包括面容、言语和动作。
但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意识并不局限于大脑的某一个区域。感知内容或感知类型不同,涉及的细胞和通路也就不同。研究神经信号的协同调动或有助于研究人员找到可靠的意识特征。2019年的一项研究收集了159名受试对象的fMRI数据,研究人员发现与处于最低意识状态和麻醉状态的人相比,健康个体的大脑中的神经信号协调模式更加复杂且不断变化【5】。
关于意识的起源还有很多未解之谜。对于如何对研究结果进行解读,科研人员总是各执己见。此外,衡量有意识和无意识始终是一个挑战,这和判断大脑接受到不同信息后发生了怎样的活动并非同一个问题。尽管如此,对各种意识水平下的大脑功能的研究至少提供了机械解剖以外的新角度。Seth表示,他希望意识领域的研究人员可以“更多地以二十一世纪的方式进行精神病学探索,从而根据特定症状背后的机制制定干预策略”。
意识调节或为疾病治疗提供新的可能The brain意识调节或为疾病治疗提供新的可能
基于意识研究的干预策略研究已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大脑损伤患者或将成为最早的受益者。例如,之前有研究指出丘脑在意识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Monti和他的同事一直在尝试使用基于超声的无创技术刺激大脑损伤患者的丘脑区域。
他们的第一个试验对象是一名25岁男性,因车祸昏迷了19天。治疗3天后,该患者逐渐恢复了语言理解能力,能够对指令做出回应并用点头或摇头的方式回答是或否的问题。5天后,他已经能够下床试着走路了。
这起病例报道于2016年,其中明确提到该患者的康复可能是巧合——有一部分患者本身就会从昏迷中自行醒来【6】。但尚未发表的后续研究却表明,超声治疗手段或许真的有效。后来,Monti团队以一名几年前发生车祸的男性患者为治疗对象,该患者因大脑损伤长期处于最低限度意识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人表现出些许对于环境或自身有意识的迹象。实验治疗几天后,患者的妻子问他是否能认出家庭照片中的人。他能够通过眼球运动做出明确回答,向上看是认识,向下看是不认识。Monti记得他在治疗后很快去探望了病人和他的妻子。“她看着我,甚至都没有打招呼。她说,‘我想要更多’。”Monti说。那是自车祸以来她第一次与丈夫交流。
由机器学习算法构建的模拟视幻觉。来源:Keisuke Suzuki/Univ. Sussex
Monti和他的同事在其他几名长期昏迷的患者身上也发现了同样令人鼓舞的结果,但目前还不清楚疗效能够持久,还是患者会在几周后重新进入昏迷状态。团队的研究仍在进行中,研究人员希望知道重复治疗是否能使治疗效果维持更长时间。“我真的认为这有望成为一种可以帮助患者康复的手段,”Monti说,“有人曾经称它为‘速启大脑’。我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速启大脑,但这个比喻却是合理的。”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神经科学家Hakwan Lau及其同事表示,进一步研究意识的发生将有助于找到更好的治疗焦虑、恐惧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疾病的手段。目前治疗恐惧症的标准方法是暴露疗法,即让患者反复暴露在他们最害怕的事物面前。这种方法的体验非常不好,因此50%或以上的患者会选择退出治疗。
相反,Lau的团队正在尝试使用基于fMRI的技术对人们的无意识状态进行调节,当特定大脑区域被激活时,人们会获得一定奖励。在一项双盲试验中,研究人员邀请了17名受试对象接受挑战——他们可以进行任何精神活动或采取任何精神策略,目标是让面前电脑屏幕上的点变大——点越大,研究结束时他们得到的报酬就越多,挑战不会对其所想的内容加以限制【7】。但受试对象不知道的是,只有当他们大脑特定区域被激活时屏幕上的点才会变大,而根据之前的大样本研究,这个特定区域只有在他们看到自己害怕的动物的照片时才会被激活,譬如蜘蛛或蛇。
随着研究的进行,受试对象能够越来越有针对性地激活特定区域,但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想到了那些自己害怕的动物。实验结束后,受试对象再看到这些动物时掌心出汗明显减少——掌心出汗反映了他们的紧张程度;杏仁核激活水平也明显降低——杏仁核区域往往在面对威胁时被激活。这种方法似乎在人们未意识到的时候改变了大脑的恐惧反应。
Lau和他的同事目前正在测试使用这种方法来治疗恐惧症,他们希望最终这项技术能够推广用于治疗PTSD。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尽管恐惧相关的身体症状减少了,但人们对蜘蛛和蛇的主观感觉却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如果你问他们是否害怕(这些动物),”Lau说,“他们的回答是害怕。”
纽约大学的神经科学家Joseph LeDoux认为要解决恐惧,归根究底可能需要同时针对无意识和有意识两条通路,二者在大脑中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他说无意识通路起源于杏仁核,但是这种对于威胁的自然反应不应该被视为恐惧。而有意识的恐惧来自认知以及对情境的情感解释,因此产生的体验并非以杏仁核为中心。LeDoux说这种差异在盲视者身上最明显,他们无法有意识地感知视觉刺激,但其行动却仿佛他们能看到一般。当出现威胁时,他们的杏仁核区域会被激活,同时出现相应的身体反应,但他们主观上并未感到害怕。
LeDoux说,这种生理反应与主观感受的不匹配可能有助于理解现有的抗焦虑药物为何对部分患者无效。这些药物多基于动物实验开发而成,可能靶向杏仁核中的神经回路,影响个体的行为,譬如胆怯程度——让他们更易于参加社交活动。但是这些药物并不一定会影响有意识的恐惧体验,这表明未来的抗焦虑治疗可能需要分别解决无意识和有意识两个过程。“基于大脑的研究方法将不同症状看作不同神经通路的产物,我们可以据此设计针对不同神经通路的治疗方法,”他说,“调低音量不会改变歌曲——只是改变音量。”
精神疾病是意识研究人员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Lau说,其理论基础是部分心理精神疾病,包括精神分裂症、强迫症和抑郁症等可能是由无意识层面的问题引起的,甚至可能是有意识和无意识两条通路发生冲突引起的。意识和精神疾病之间的联系到目前为止仅仅是假设,但Seth一直在利用“幻觉机器”探索幻觉的神经基础;“幻觉机器”是一个虚拟现实程序,通过机器学习模拟健康人脑的视幻觉体验。经过实验,Seth及其同事已经证明这种视幻觉体验与服用致幻药物后的体验相近,致幻药物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研究意识的神经基础。
如果研究人员可以发现幻觉产生的机制,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对大脑相关区域进行调节,进而从根本上治疗精神异常——而不是仅仅解决症状。另外这项研究通过展示人的感知是多么容易被操控,证明了所谓的现实感不过是我们对世界体验的一个方面而已,Seth补充道。
期待堂堂正正地走上科学红毯
每年,美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全身麻醉期间恢复意识。他们不能动弹或说话,但可能会听到说话声音或设备噪音,也能感受到疼痛。这种经历可能具有创伤性,因此相关医生必须承担相应的伦理和法律责任。部分科学家正致力于推广相关指南,指导与无反应患者进行沟通,并设法寻找此类患者出现不适的迹象。此外,他们也呼吁增强专业培训和制定法律条款以应对这样一种可能性:新的意识检测方法或将改变医疗操作中“知情同意”的定义。
研究人员也开始重视与社会公众的沟通,解释意识科学能够和不能够实现什么。Michel说,意识研究中出现了大量没有实证数据支持的论断。其中特别突出的一个被称为“整合信息理论”,虽然Michel和意识研究领域内的其他专家都公开否定了这一理论的合理性,但相关研究仍获得了大量的私人资助和媒体关注。在2018年一项针对249名研究人员的非正式调查中,Michel和他的同事发现,大约22%的“非专家”(即没有发表过意识相关论文,也未参加过重要的意识相关会议的人)相信整合信息理论【8】。Michel推测“大师效应”(Guru Effect)可能是罪魁祸首,即 “非专家认为业内权威所做的复杂模糊的论断比那些较为简单的理论更有可能是真的。“在某种意义上,理论的复杂性被用来代表理论为真的可能性,”Michel说,“他们并非真的理解某个理论,而是认为如果自己真的理解了,可能就会把它当作正确的意识理论。”
为了巩固意识科学的正当性并鼓励科研人员及公众接受循证意识理论,Michel和来自其他多个学科的57名同事,包括Seth、Lau、Goodale和LeDoux,对上述非正式调查做了进一步的随访,并于2019年发表论文对意识研究领域的现状进行了概述。他们的发现喜忧参半【9】。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目前尚未承认意识研究的战略意义,他们写道。该领域创造的就业机会明显落后于其他新兴学科,如神经经济学和社会神经科学。关于意识科学研究的公共资助相对匮乏,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明显。但意识科学的某些方面已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自本世纪00年代中期以来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已为多项相关研究提供了资金支持,研究内容包括有意识与昏迷状态之间、清醒与睡眠状态之间的神经学差异等。这些研究或可以为我们打开一个窗口来了解意识的神经特征。Goodale表示部分主流私人慈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也在为意识领域内的重要研究课题提供帮助,他本人就从一个类似的组织——加拿大高级研究所获得过研究资助。
随着研究资金和研究发现的不断积累,意识相关内容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科研人员的研究计划中,即便目前尚不是核心内容,至少其存在是合理正当的。“意识科学正在逐渐向神经科学、心理学、医学等标准化成熟领域靠拢,”Seth说,“学科研究正在逐步规范化,这是让人欣喜的一件事。”
参考文献:
1. Owen, A. M. et al. Science 313, 1402 (2006).
2. Monti, M. M. et al. N. Engl. J. Med.362, 579–589 (2010).
3. Casali, A. G. et al. Sci. Transl. Med. 5, 198ra105 (2013).
4. Siclari, F. et al. Nature Neurosci. 20, 872–878 (2017).
5. Demertzi, A. et al. Sci. Adv.5, eaat7603 (2019).
6. Monti, M. M., Schnakers, C., Korb, A. S., Bystritsky, A. & Vespa, P. M. Brain Stimul.9, 940–941 (2016).
7. Taschereau-Dumouchel, V. et al.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5, 3470–3475 (2018).
8. Michel, M. et al. Front. Psychol.9, 2134 (2018).
9. Michel, M. et al. Nature Hum. Behav. 3, 104–107 (2019).
原文发布在2019年7月24日Nature OUTLOOK上,作者:Emily Sohn
?
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2207-1
版权声明:
本文由施普林格·自然上海办公室负责翻译。中文内容仅供参考,一切内容以英文原版为准。欢迎转发至朋友圈,如需转载,请邮件China@nature.com。未经授权的翻译是侵权行为,版权方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
? 2019 Springer Natur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